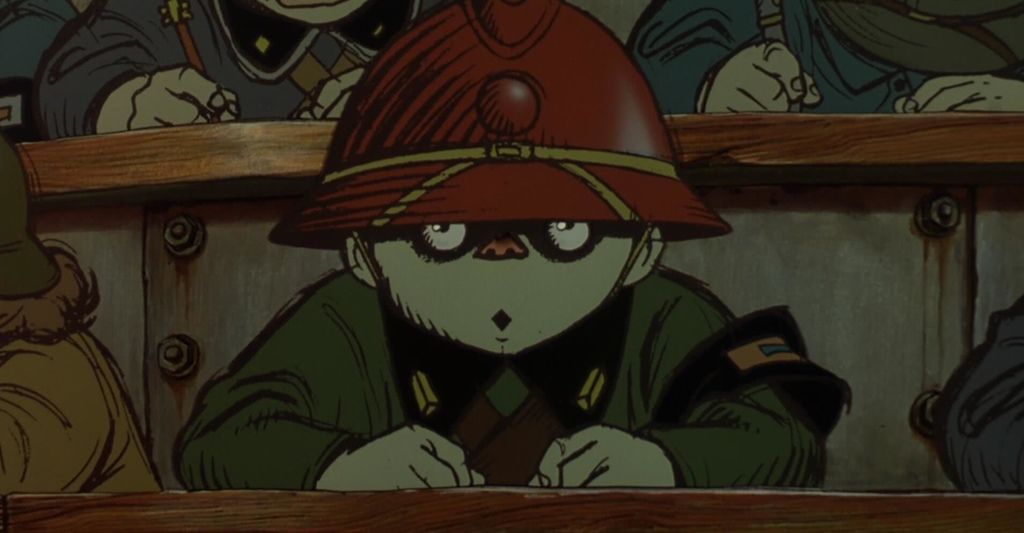「既然我都能忍受了你和媽媽的吵架,為什麼你們不能為了我而忍受?」蓮子(田畑智子)因著父親(中井貴一)搬離家中,幸福家庭的想像在剎那間頃倒。她把父母關係的不能持續,歸類為他們「不願忍受」,把她的不滿藉著問題拋給父親,換來父親的沉默。
相米慎二的《搬家》是1993年的作品,透過小六生蓮子的日常生活,以至帶有奇幻的歷險,直視兒童如何面對,以至梳理摯親關係的破裂。在離異漸成普遍的年代,蓮子的故事並不罕見。
甫開場,三人在家裡吃飯,夫妻各自佔據三角餐桌的一邊,尖角直指向鏡頭,就如刺穿了家庭的和諧表象 ──沒有太多交流,僅有的對話也夾雜著不耐煩,衝突一觸即發,坐在中間的蓮子如常像一個小大人般與跟父母說話。這場幾分鐘的晚餐戲,除了揭示這個家庭的關係即將生變,也暗示過往被父母寵愛的蓮子,將面臨巨大的衝擊。
一個小六學生怎樣理解父母離異,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。擺在眼前的事實是,父親搬往新的住處,不再與她們同住;她與媽媽(櫻田淳子)雖然留在舊居,但重新訂立的家規,也是新生活的明證。不愉快的夫妻的生活,沒有可能於小孩前掩藏,蓮子的不滿,或者在於她以為父母的爭吵,就如她跟他們鬥氣一樣,是可以被接納的、被原諒的,沒還想到存在分開這個選項。
在父親遷出之前,以至往後的一段日子中,蓮子如常過活,抱著他們和好的期望。她偷偷跑到父親的家,陪著父親燒掉舊物,又跟媽媽吃了慶祝大餐,彷彿一切如舊,甚或藉著他們關係的空隙,遊走在二人之間,擁有以往沒有的自由。但是,從細節一看,就見事情不如想像般簡單 ── 父親把三人合照燒掉,蓮子企圖自行從火堆取回;母親重新規劃家務的分配,蓮子不滿因而撕破時間表,這些舉動都證明父母對新生活的期待,與蓮子的想望不同,致使生活上的張力逐漸浮現。
這種張力同時在學校出現。一直在眾人眼中有著美滿家庭的蓮子,除了向一、兩位相熟的同學坦白外,根本無法承認家庭出現變化,因單親小孩就像異數 ── 有同學被欺凌,就僅因父母離異。當父母和好漸無可能,同儕之間的相處出現隔閡,平日爽朗的蓮子無所適從,最終壓力跨過界線,行為愈見偏差。
《搬家》的焦點在於女孩面對家庭突變的回應,前段細膩與平實得彷彿跟著蓮子,面對家庭的破滅,叩問她應該如何自處;直至電影的後段,風格突然一變,藉著蓮子因慶典走進山林,這疑幻似真的經歷,終究成就她的蜕變。
蓮子策劃了琵琶湖之旅,希望能夠一家團聚,卻終究發現期望落空。她挾著憤怒、無助與失望,逃離了父母的視線,在路上遇上一個老人與他的女兒,又在慶典後一人走到山上。她整晚獨留山野,一人在河溪發呆,在冷卻的火堆邊睡覺 ── 這次行動,在鏡頭下帶有一種魔幻感,容讓她排解這段時間的各種情緒,消化父母離異的事實。
火的意象也在電影一再出現,並在這個晚上也到達了高峰。父親燒掉舊物時的火光、蓮子因被壓力壓倒後的行為偏差、期望與父母一起觀看的「大文字燒」慶典,而這一晚,她直接走上山頭近距離觀看其他人的慶典的火堆,更在夜之將盡,日頭初起的時候,一人站在湖邊,「望著」曾與父母玩樂的畫面,又隨著火燒渡船而消失。每一場火都指向蓮子的心理變化,從一開始的拒絕接受,至看著代表過往回憶的渡船被燒毀,終能明白有些事情已經結束。
相米慎二的《搬家》震撼,在於他刻劃兒童面對父母離異的不安與憤怒,藉著蓮子的反應,呈現孩童面對家庭變異時的情緒,而田畑智子的演出,也演活了蓮子的神髓 ── 她無助、痛苦、不惑,同樣倔強、暴烈;性格不完全討好,有時叫人憐惜,有時叫人頭痛。然而,這不就是一個十一、二歲的兒童,面對最熟悉的家人分離的反應嗎?
若然夫妻經過一段磨合不果,最終選擇離異,仍需要時間平復,那麼對於只得被動地接受的孩子,又應該如何處理?相米慎二交出的答案就是,給予時間容讓他們消化,這是一個過程 ── 夫妻磨合是一個過程;磨合不果至分離是另一個過程,而對父母離婚的孩子來說,接受家庭的不完整也是一個過程。過程不必然容易處理,甚至比兩個成年人的爭吵,需要花上更多的心思 ── 畢竟,每一個經歷父母離異的孩子,不多不少有無法修補的缺口,靜待時間癒合。